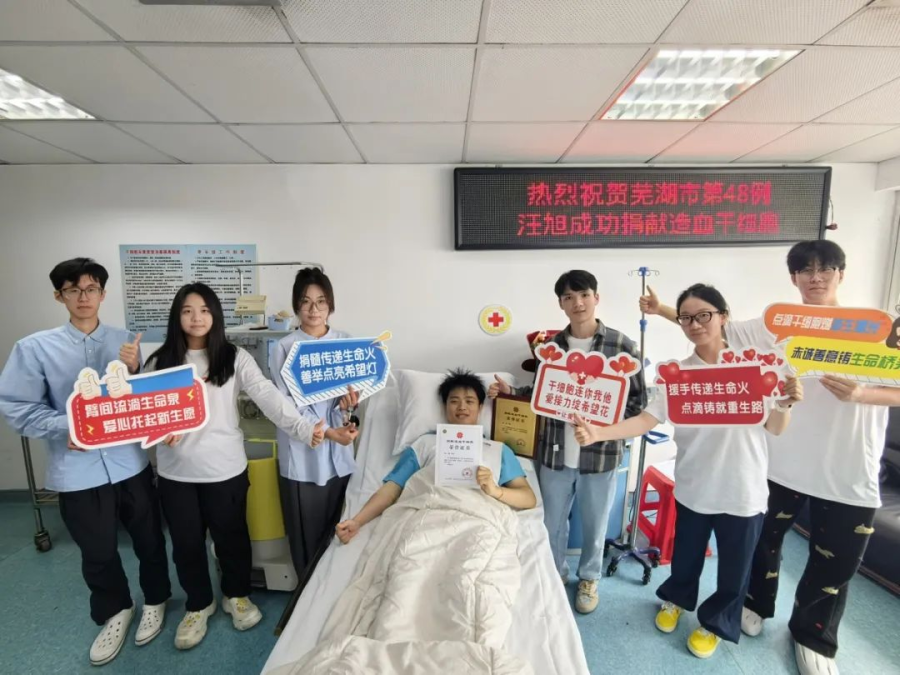安徽省重點新聞門戶網站
安徽省重點新聞門戶網站
 安徽青年報官方網站
安徽青年報官方網站
徽州古城:磚石間的千年徽韻解碼
踏入徽州古城,青石板路泛著溫潤光澤,白墻黛瓦在檐角勾勒出水墨輪廓,許國石坊的八柱雄姿刺破天際——這座藏于皖南群山間的古城,正以磚石為箋、歲月為墨,書寫著徽文化的千年史詩。

徽州古城標語(圖片:陳佳琦)
徽州古城的根脈,可追溯至秦代設“歙縣”的郡縣煙火。唐宋以降,徽商踏遍山河,科舉考場走出無數簪纓:“連科三殿撰,十里四翰林”的佳話,映照出“東南鄒魯”的文運昌盛。
許國石坊是這段歷史最驕傲的注腳。萬歷年間,功勛大臣許國衣錦還鄉,朝廷特賜這座全國唯一的八腳牌坊。四柱三門的常規被打破,八柱四面的形制如巨人屹立,柱身“巨龍盤繞”“錦禽爭鳴”的石雕分毫畢現,額枋上“恩榮”“大學士”的字跡仍透著威嚴——它不僅是個人榮耀的象征,更是徽人“賈而好儒”精神的凝固。

八腳牌坊(圖片:衛珍)
古城的每一塊磚石、每一道雕紋,都蘊藏徽派建筑的“密碼”:石雕是大地的絮語:許國石坊的須彌座刻滿纏枝蓮紋,漁梁壩的條石歷經千年水擊仍嚴絲合縫;木雕是木梁的歌謠:民居隔扇上“松鶴延年”“耕讀傳家”的圖案,以鏤空技法雕出層次,陽光穿過時投下流動光影;磚雕是門樓的詩行:門楣上的“福”字磚雕,以深淺浮雕疊出立體感,連磚縫都藏著“步步高升”的寓意。
漫步斗山街,魚骨狀街巷串聯起數百年老宅:天井聚水藏風,馬頭墻錯落如琴鍵,府衙遺址的殘垣仍能想見“坐堂問政”的往昔——古人將風水智慧、家族倫理,全刻進了建筑的筋骨里。

徽州府(圖片:丁依佳)
徽州古城從來不是“標本式”的存在,而是文化基因的“活態容器”:徽劇的水袖仍在翻飛:老藝人在古戲臺演繹《水淹七軍》,唱腔里藏著京劇的源頭韻律;徽菜的煙火仍在蒸騰:臭鱖魚的發酵香飄滿巷弄,毛豆腐的焦脆里裹著山民的生存智慧;非遺工坊的刻刀仍在游走:石雕傳承人程師傅守著作坊,將古牌坊的紋樣拓印成文創書簽,學徒們用3D掃描技術復刻失傳圖案......

徽菜養生宴(圖片:丁心茹)
新安畫派的水墨遺風,徽州篆刻的金石氣韻,甚至市井間的方言吆喝,都在證明:徽文化從未遠去,而是以新的姿態滲入生活。

《徽商情韻》(圖片:周微)
清晨,賣早點的推車碾過青石板;午后,茶館里老人聊起徽商往事;黃昏,年輕人在文創店設計“徽韻”主題盲盒......古城的活力,都暗藏在這些日常里。
如今,“修舊如舊”的保護理念讓老建筑重煥生機:廢棄的糧倉改造成非遺展館,老祠堂里辦起徽劇工作坊,甚至“數字復原”技術讓損毀的雕刻“虛擬重生”。游客穿梭其間,買一塊徽墨酥,聽一段非遺講解,觸摸的不僅是磚石,更是文化傳承的溫度。
徽州古城是一部攤開的史詩,每一塊磚石都在訴說過去,每一縷煙火都在擁抱未來。當現代文明與千年古韻共鳴,這座城終于證明:真正的傳承,是讓歷史活在當下,讓文化流向遠方。
(丁依佳)
責任編輯:李志慧

- 2025-07-09 科技逐夢 翱翔藍天 合肥市育新小學學子獲無人機應用編程場景賽省級榮譽
- 2025-07-09 合肥市育新小學健兒閃耀廬陽區陽光體育跳繩賽場勇奪多項桂冠
- 2025-07-09 智慧指尖展風采 合肥市育新小學學子2025年中小學生魔方比賽獲區級榮譽
- 2025-07-09 深析聚能促教 分層聚力共進 合肥市育新小學英語組舉行期末質量檢測分析會
- 2025-07-09 安慶市外國語學校初中部東區開展暑期家訪活動



 贊一個
贊一個